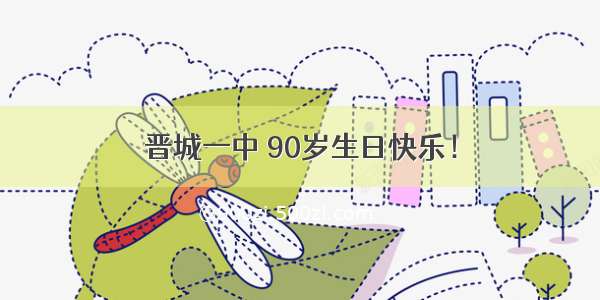导言
本文为晋城一中1965届校友张荣堂倾情撰写的清晰刻画、感人记叙母校生活和师生友谊的忆文,其中提到母校教学史上著名的胡敬虞、黄克伦、胡荣绵、郝勤章、刘树魁等名师课堂上的教学方法及对学生们一生的影响,至今看来依然可另后辈受用。也有对时年母校校舍分布、课外下地劳动和宿舍生活的描述内容,写实中充满着意趣。也有对60年代晋东南地区民间生活中常见的磬碗、米萁、灶火等地方风物的真实描述。极为珍贵,可贵,现与大家分享。
作 者
张荣堂,晋城一中1962届初55班、1965届高31班校友,现居北京。
我记忆中的一中
昨天接到晋城老家同学的电话,说我就读过的晋城一中高三十一班,准备举办一次同学聚会。这消息一下激活了我尘封的记忆,往事如潮水般在心中翻卷,记忆冲开心门如泉水似的涌向笔端。
我是1959年从晋城师范附小考入晋城一中的。当年的一中是我们晋东南的名校,它的高中部从晋、高、阳、陵、沁五县招生,从这五个县的初中毕业生中掐尖招收优秀学生。可以想见,能考进一中,对当年的我来说,是很满意的。
优雅的温老师
入校后,我被分配到55班。那一届初中共招进4个班,从53到56。班主任是温润芳老师。温老师是天津人,从天津某大学毕业后,分配到我们这里,教我们数学兼做班主任。记忆中,温老师是早我们一年来到一中的,56班的班主任刘老师是她的同乡,也是她大学的同学。温老师性情温柔,举止言谈、穿着打扮,迥异于我们这太行山区的人。她当班主任时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,与她接触多一些。她的兴趣、爱好,对事物的理解,对事情的态度,对人的判断和评价,对我都产生了影响。印象里她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精力充沛、身形健美,走路出奇的快。习惯了我们本地人的慢动作,对她这风一般的行走,总有一种异样的不解。
温老师面目俊雅,加上白皙的皮肤,显得总是那样干干净净。那个年代不兴奇装异服,可温老师的衣着一看就不是我们本地人,无论新旧都可身合体,衣服的样式也显有特质,有别于我们这乡土气息。
有时她讲完课,坐在讲台上,监督我们完成练习。我做完习题,偶一抬头,看着静默中的她,不禁联想开去:是什么样的环境培育了温老师这样的人?从地图上看天津在海边,天津是什么样子?听说那里有高楼,有外国人居住过的租界地,有外国式样的房子,有大公园,还有海河从城市里穿过······对于从未走出过大山的我们来说,这些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。是温老师这些外来教师,这些言谈举止迥异于我们本地人的师长,引发了我们对外界的想象,撩动了我们飞出去的欲望。
60年代的学习生活
初中55班的学生,一半来自县城,一半来自农村,全都住校。学生宿舍在学校最东边的高台上,数排人字架的平房,从南至北排列,全部砖瓦结构。每排大约有4个寝室,每个寝室都是3个间段。寝室门开在北面,南面有窗户采光。室内东西两边是用厚木板架起的两张大通铺,每张铺上要并排睡上10个人,被褥一律自带。
通铺中间的空地上,有一个地火。地火是我们晋东南的一种特殊取暖设施。晋东南盛产无烟煤,尤其在旧泽州府辖的几个县,冬季取暖,只要在家里砌一个灶火,靠火焰散出的热气,便可安度寒冬。在学校,学生宿舍和教室人员密集,为节省地方,或许也为了安全,就在地上挖出一个方坑,砌下灶火,地上只留出火口,让火焰外泄。其它的过程都在地下进行,只需每天或几天一次掀开地板,将炉渣清出。
记忆中我住在3排2斋,同室的有马晓红、裴小锁、秦雍庆、李小林、任小川等。宿舍里自然是没有卫生间的,每个宿舍配一马桶。我们那里叫尿桶,听起来不雅,却也凸显了我们山区人直白的品格。一只马桶供20个小伙子一夜使用。现在想起那时的情景,还觉得难以置信。半夜几个人同时起夜,几张睡眼惺忪的脸,围着一个脸盆大的桶口,竟没有一滴尿撒在外面。哗哗的水声,应很震耳,可熟睡的人们却丝毫不受影响。均匀的鼾声,说明他们香梦依旧。凌晨起床号吹响时,两名当值的同学,抬着盛装的马桶,走过上百米的距离,到东南角的露天厕所,为马桶减负。这些在今天的人看来多少带点蛮荒的行状,那时的我们却做得认认真真、一丝不苟。
学生上课的教室,全部建在校园第二台基上。当时的校园,东高西低,东西落差较大,被分成三个台面。学生宿舍所在的地方最高,为第一台面。从第一台面顺着砖砌的台阶走下来,就到了教室所在的第二台面。所有的教室、教研室、实验室、化验室、图书室,都建在这个台面上。记忆中教室宽敞明亮,高且方正的讲台、乌漆明亮的黑板、整齐有序的课桌,连同那一声声、一句句的谆谆教导,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,成了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。
我记忆中的老师们
我是1962年从初中55班考进高中31班的。进入高中后对学校的理解就深入了些。意识到好的学校首先是有好的老师。
离开一中到现在已有50年了吧,我依然能张口就叫出教过我的老师的名字。讲数学的胡敬虞老师、教化学的黄克伦老师、教物理的胡荣绵老师、教政治的郝勤章老师、教语文的刘树魁老师等。这些师长都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,教书兼育人。
胡老师上数学课时,常讲一些看似与数学不沾边的话语,有一句是他经常重复的,叫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。我当时对这句话只作了浮浅的理解,认为是要我们准备好圆规、量角器。后来才逐渐领悟到,这“器”指的是知识、是学问,“利其器”是要求我们把功课学好、学透,融汇贯通、烂熟于心。只有这样毕业后才能胜任工作,做到“工善其事”。像胡老师这种雨过无痕的育人方法,老师们是在不经意间进行的,学生是在不经意间接受的。没有正襟危坐的道德说教,也没有夸夸其谈的思想灌输。
高三时,学习已经很紧张了。迎战高考,考不考?考什么学科?报什么专业?客观上是在规划自己的人生。我至今还记得在高三的一堂政治课上,老师给我们讲到的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。“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,必经过三种境界:昨夜西风凋碧树,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。此第一境也。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此第二境也。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此第三境也”。这些用文学语言讲出来的人生境界,既高尚典雅又形象生动,如春雨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。从那以后,在人生的途路上,我常常停下脚步,思考这些话的含义。它使我征服了横亘在面前的高山,跨过了一个山峰又一个山峰,迈上了人生的至高点,让生命绽放了它应有的绚丽。
也许是由于地域水土或文化历史的缘故,一中的老师有时显得僵硬刻板,不会变通。高中时班上有一个女同学,叫翟梅星,常在课堂上睡觉。有一次,她和同桌的男生都睡着了。老师看到后,中断了讲课,提高嗓门喝道:“翟梅星,你们俩就一起睡吧!”睡觉的当然被惊醒了。全班哄堂大笑。不是因为他俩被叫醒,而是同学们特别是男同学,从这“一起睡吧”里品出了另一层意思。可刻板的老师却未意识到,依然一脸的肃然,硬是把翟梅星叫起来,要她回答问题,分明是叫她难堪。这翟梅星同学也不是凡人,对老师的提问,对答如流,把她睡梦中老师讲过的内容,大都说了出来。按说这是个特质生,理应特殊对待,可老师却不会变通。印象中翟梅星眼睛很小,但特别有神,对视时有灼人的感觉。
同学少年都不坏
记不清是高二还是高一了,我和一个叫杨玉梅的女生坐同桌。杨玉梅冰雪聪慧,又天生丽质,每天都像化了妆似的。在那个年代、在我们那个地区,是不会有人化妆的,何况是中学生。杨玉梅学习好、人也温柔,就是爱哭。大事小情,只要遇到些挫折,就哭将起来。印象中大部分时间,他那张脸都是桃花带露,总有一滴泪珠挂在腮边。在我们班的女生里,像杨玉梅这样的,还不是男生追逐的对象,因为比起杜元鄂和朱素贞的漂亮来,她还只能叫做好看。
男生中我最不该忘记的是候金山。高二时他是我们的团支书或班长。现在提到他,心理还隐隐的发憷。怎么说呢,在我的心目中,它既是令人敬佩的保尔·柯察金,又是叫人生厌的“催命鬼”。人长得黑瘦枯干,可身上有使不完的劲,能吃苦,凡事都冲在前面,学习也不拉后。作为班头,他是称职的。可凡事都有个度,太执着了,就容易错位,做出过火的事。
我们上高中时,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。学校在城北的白马寺山开荒种地,每班都分有责任田,一到周日就下地劳动。最难的活是从城里往山上运肥料,每人要挑上近80斤,爬10多里山路。这对农村来的同学可能不算什么,可对从小在城里长大、没有干过农活的同学,就难了。可班头候金山不管这些,每次劳动他都叉着腰、黑着脸,监督着每一个人,表现得比班主任还班主任。平时和同学相处,也不苟言笑,记忆里很少见他笑过。
在我们班有不少学习成绩特别突出,只因为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的原因,不能通过政审,被挡在了大学门外的同学,至今回忆起来,为他们抱屈。丁佰禄上初中在53班,后来参加初升高考试,他考晋东南第一。此人思维敏捷、记忆力超常,在我们班学习是拔尖的。尤其是数理化,课堂上老师提问,前面几人回答不出,或者回答不全的,最后都要叫他。他的回答言简意赅,一语中的。当时中科院数学所发行一种叫《数学通报》的杂志,我们班喜欢数学的同学都定了来阅读,每期的一些数学难题,他们都能鼓捣出来。就这么一个很有科研潜质的人才,一个有可能发展成科学家的苗子,却因为父亲的一些问题,被政审所困,只能望大学而兴叹。
学校的第三台面是大礼堂、食堂和后勤服务部门。大礼堂是学校举行盛大活动的地方。诸如开学典礼、毕业典礼、上级领导及社会名人来校作政治报告、学术报告、全校举行文艺演出,都在这里进行。著名作家赵树理就曾在这里作过报告。礼堂的设施很简陋,砖砌的舞台,台下没有座椅,临到开会时,搬来条凳,一行行摆起来。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,一场场活动进行得有声有色,尊严肃穆。
学校就一个食堂,要供千余师生就餐。要按现在的吃法,那是万万做不到的。那时吃的是大锅饭,长廊似的食堂里,一溜支着十几口大铁锅,一口锅一顿要做出供一个年级吃的饭食。这饭怎么做?做好了怎么来吃?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。好在我们晋东南人好吃稀的,什么米萁呀、菜粥呀,我们都常吃不厌。吃饭的情状就更是一景了,每人端着一个粗瓷大碗,我们叫磬碗。这碗的大,外人都难以想象,唯我们晋东南独有。先排了队,到自己班级的大锅旁去盛了饭,再到食堂外面的空场上,顺势一蹲,便呼啦呼啦的吃起来。千数个人头、千数只大碗,黑的头、白的碗,那场面是很壮观的。而今,我们都到了迟暮之年,想起当时的吃饭,或然就胃口大开。
往事如烟,我握笔坐在寓所的窗前,望着窗外异乡的楼宇、田舍,忽然就有了“日暮乡关何处是”的感慨。
老猿 写于北京 嘉园三里